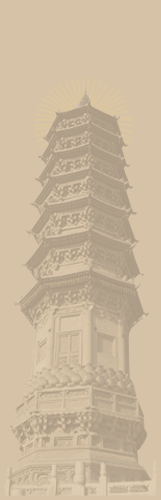作为柏林禅寺的一名僧人,我深以赵州和尚为荣。赵州和尚在禅方面的造诣,雍正皇帝以“圆
证直指”来概括。黑漆桶如我于禅尚未入门,但读赵州语录仍然能隐约感受到那种截断语路,直指
人心的力量。而“吃茶去”公案则开启了“茶禅一味”的先河,由此孕育出灿烂的禅茶文化,覆萌
无数众生。
生命念念常新,是活泼泼的。这是一个毋需论证的真实。在这里,一切理论、言谈、造作、追
寻俱显多余与苍白。禅正是在这里拯救了我们,茶也正是在这里封上了我们的嘴,把我们带入静默
的当下。这一杯茶,也是亘古常新的,它似乎就是人类几千年、几万年上下求索的最终答案。尤其
在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陷溺于五欲尘劳,在浮尘光影中迷失了自心的时候,赵州和尚的“吃茶
去”让我们跳出来,与佛祖相见,与心性本来相见。
张菁 居士发心编著的这本书荟萃了赵州和尚禅茶智慧所衍生的古今中外的诸多大事因缘,它
也使我想起自己在柏林禅寺所亲历的茶的故事。
那还是一九九三年四五月间,我出家还不满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傍晚,一辆东风牌大卡车满载
茶苗停在赵州塔西边当时的“问禅寮”门口。车上下来的,一位是当时云居山真如寺的当家明道法
师,还有一位居士,另一位就是家师净慧上人。几天前,他偕明证、明树上云居山请茶苗,茶苗用
汽车装好,他撇下两位侍者,让他们坐火车,自已亲自押车。三千里路云和月,伴一车绿葱葱的茶
苗从“赵州关”回到赵州祖庭。那一年师父恰好六十岁。
车刚停稳,师父跳下车也不休息,就招呼我们卸茶苗。师父是个干活的能手。他把我们分成两
组,一组从车上卸苗,一组由他和明道师父亲自指挥在问禅寮院子前的地上栽种。师父说,茶苗已
经在路上颠簸了几天,离了地气,得赶紧载好,浇水。因为人多,一个多小时的工夫,几千株茶苗
就移民到这发源了“赵州茶”的土地上。
我那时简直是个懵懂少年,不懂茶,更不懂赵州茶,当然也不懂师父“南茶北移”的用心。只
是觉得师父的行为象个浪漫主义派的诗人,有些好笑。稍后我又知道,师父当时移载的这一片茶苗
是当时中国纬度最北的茶,把茶苗种植的纬度北移了一度多。茶树北移的实验就这样由赵州柏林寺
的老和尚开始了。
这实验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师父百般呵护,出门在外也要打电话嘱咐我们照管好茶苗;虽然
我们抽调了擅长种花的明吉师父专职看护,赵县一位精通农业技术的副县长何英敏也三天两头来看
望这些“江西老俵”,为他们的生计出谋划策,但是这些茶苗就象被瘟疫击中的一个村落,又象抵
抗强敌、寡不敌众的一支部队,相继萎黄、死去。到第二年夏天,剩下十几株,然后是几株,最后
是一两株,最后……。何英敏县长想了许多方法,譬如施特殊肥料,罩棚等等。等他最终找到问题
症结的时候,茶苗终于也死光了。
师父也没多说什么,他仍然处在惯有的静默中 , 每天做他要做的事。他在心里坦然接受了失
败。
这次实验却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是何英敏县长的朋友,当时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所长张占义。
张占义是河北灵寿人,先后做过县委宣传部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后来被调到省农科院。他
为人爽快、仗义,让人想到太行山,想到曾经在电影上看过的某一位游击队英雄。
在我们的实验失败之后,何县长几次陪张占义来寺,谈论茶树北移的事。张占义扬言:非再一
次尝试,搞成功不可!我们总是报以怀疑的一笑 , 对他的话也未太当真 . 反正,赵州茶不一定是
指某种具体的茶。
终于 , 在一九九七年的某一天,张占义又一次来寺,说几天后启程到江西云居山请茶苗,想重
走师父当年的旧辙。我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云居山真如寺的监院衍真法师。衍真法师是我大学的
同学,上学时学佛的同修,毕业后,各奔东西,不通音讯。师父上次请茶苗时作了我们两人的信使,
互相才知道毕业后心心相印,走了同样的道路。
再后来,张占义从南方请回几万株茶苗,在太行山区试载。因为那里雨水相对丰沛、土壤碱性
也略低。再后来是 2001 年,张占义又一次来寺,报曰:试种在灵寿的几亩茶园经过三年的努力,
成功了!请我和明安师去采摘、炒作。于是这一年 4 月 22 日,我和从云居山回来的明安师有了
太行山之行。
张占义实验的成功将当时中国种茶的纬度北移一度,在媒体和茶叶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可惜,
因为资金缺乏,跟进措施不力,迄今尚未在太行山区大面积推广。
张占义兴致勃勃地忙于茶树移载的那段时间,我们每次见面,总要讨论“赵州茶”的虚实问题。
不管我怎样“谈禅论道”,他坚持认为“赵州茶”一定实有其茶。我嘴上一边解释,心里一边暗笑
他的迂。直到有一天,这燕赵好汉突然扔给我一条资料,顾元庆《茶谱》品司条载:“今茶产于阳
羡,山中珍重一时,煎法又得赵州之传,虽欲啜时入以笋榄瓜仁芹藁之属,则清而且佳。因命湘君
设司检束而前之,所忌真味者,不敢窥其门矣。”由此看来,赵州茶非仅是茶之禅,而且也是禅之
茶 . 真正是茶禅一味,天下赵州矣!
2005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