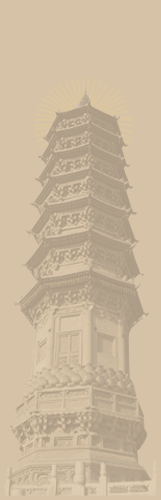以前看徐志摩的传记,他提到上海的生活。大意是:上海是一个大染缸,当你身在其中时,感觉不到什么异样,但当你跳出来重新审视,就会发现生活原来不该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说的是霓虹声色的上海,也是说整个娑婆世界。
当火车窗外的景象渐渐开阔,田野绵延无际,当天色逐渐转暗,漫过荒凉的草坡和森森的山体,我知道,自己已从繁华世界中出走,去向是柏林禅寺。
行前,朋友们不解,似乎一个年轻人本应与寺院无缘,而你去泡吧、去 K歌、去网游,没有人会奇怪。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何妨跳出来看看呢。
我只对朋友说,我去清洗一下自己的镜子。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镜子,如果镜面染尘,甚至变形断裂,照出的景象也会随之黯淡变异。于是世上有了贪婪的人、嗔恨的人、迷惘的人,或被过去的印象所牵绊,或被现在的假象所蒙蔽,或被将来的幻象所诱惑。
一位女诗人说: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而我相信,生命的本相是单纯而清明的,要让灵魂重回清澈和圆满,需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所以走出城市。这次朝圣之旅,多年的好友志旻和我在一起。
让我们认真面对自己的镜子吧。
到石家庄会有生活禅夏令营的义工来接站,不会没方向,如同到家。入夜的车厢里空调很冷,志旻把他的衣服给我,自己盖着毛巾,我们仍然觉得寒气袭人。颠簸疲倦,我看着身边瞌睡的志旻,心里却很安宁。
彻夜不眠。列车在浓重的夜色中摸索,过了江苏,过了安徽,过了河南。想起台湾一个学佛的诗人周梦蝶写道:
有金色臂在你臂上扶持你
有如意足在你足下引导你
憔悴的行人啊!
合起盂与钵吧
且向风之外,幡之外
认取你的脚印吧
最起初,只有那一轮山月
和极冷极暗记忆里的洞穴
然后你微笑着向我走来
在清凉的早上,浮云散开
——席慕蓉《历史博物馆》
早上的石家庄站,还没到接站时间,已经有一位法师和几个义工在等候,志旻和我走上前去,彼此的目光稍一探询,就互相明白。
在清凉的早上,浮云散开。
他们微笑招呼我们,搬来凳子,倒上茶水,问候车马劳顿。法师是个中年人,土黄衲衣,周身尽是淡淡的温和。他说,寺里接站的车每天发三次,等一个小时左右,接到五、六个营员就可以发车了。正说着,他的手机骤响,他接起来就说“阿弥陀佛”——如同我们说“喂”——然后才交谈。我初次听到有人这样接电话,很觉新鲜。后来到了寺里,各位法师和居士都用“阿弥陀佛”相互招呼,也就习以为常,每次听到对方一声佛号,未语心先安,接下来的谈话也就和风细雨。
.当时我们坐下喝水等待,义工拿出柏林寺的书刊给我们,聊当解闷,见我们手里拿了书,又搬过凳子来安放水杯。等了一阵,见我们面色疲倦,就引我们坐上车休息。
如此种种,我暗自感叹他们的细致周到。平时见惯了各行其道、神色漠然的人群,对无偿的体贴反而有些大惊小怪。人非生而知之者,柏林寺究竟有着怎样的磁场,让生活禅的成员都透出温煦的风范?
暂时没有答案,我和志旻钻进车子里补睡。不久就陆续来了些人,车子向赵县驶去。我打着瞌睡,朦胧只见身边坐着一个胖女孩,一身黑衣,正襟危坐,似乎并不可亲,我们也没有任何交流。
车子开进赵县,路面左右颠簸,我才发现这是个简陋的小县城,不禁对夏令营的生活条件开始担心。在近寺院的地方,耸立着一个石雕经幢,表明柏林寺曾经的痕迹。一个多年为夏令营出力的义工介绍说,柏林寺过去规模宏伟,今寺的面积,只相当于古刹的一个观音院。后来读到马明博居士的《天下赵州生活禅》,原来在古时,这里已经是一个鼎盛的道场,它的法乳还曾滋养过西天取经的玄奘。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初的原貌已经模糊,却仍向四面八方辐射精神力量,上海感受到了,北京感受到了,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了感应,于是我们这些可能永远彼此陌生的年轻人,在同一个时间,来到同一个地方。
有些因缘让人顶礼。
进了寺门,依次下车,马上有义工从车上卸下我们的行李,帮着搬运。从长廊穿过,直至客堂,也早有人等候为我们登记身份、分发服装、预订回程车票,手续简明而周到。然后我们被接引到各自的寮房休息。至此我和志旻分开了,我们将各自去结善缘,我去女营员入住的云水楼,他到男营员下榻的古佛庵。
寮房里已经有人,都是温婉的女孩,早在前两天就来亲近法音。六张床位,各系一顶蚊帐,凉席,薄毯,朴素井然。这景象如同一阵凉风,吹散了一路劳顿和犹疑。展开营员服装,雪白的 T恤上有一行字: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正是此次夏令营的主题。更换着衣服,我也逐渐明白,这里的环境虽然朴素简单,但也是善意的安排,为此许多人付出心力。所以,面对一盆一钵,我们也该放下分别计较,且安然,且感谢。正想着,衣服换上了,轻透柔软,非常舒服。
同车而来的黑衣女孩,名叫晓松,也分在这间寮房。再次见她,我们相视微笑,车上彼此不闻不问的陌生感渐渐融化。每个人都如同本来精彩的视频文件,而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就像打开文件的程序,程序不对时,文件在你看来只是一团复杂难懂的编码,一旦有了合适的程序去解读,对方的音容乃至心声都鲜活起来。我想,“生活禅夏令营”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程序,让陌生人真正相逢;这个程序还非常广大,让我们和世界真正相通。这正如《红楼梦》中所道:“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
在寺里,吃午饭称作“过堂”,打板过后,僧人和居士就在斋堂前分门等候,鱼贯而入,如礼如仪。初次见识,觉得很新鲜,尤其是饭菜都摆上了还不能吃,大家都要诵经,我当然不会,甚至听不懂那些法师居士在唱什么,只有双手合十,眼睛却盯着饭碗。
终于开饭,众人低头专注下箸,鸦雀无声,原来连吃饭也充满了庄严气象。一个行堂师傅走来,抱着一个盛满馒头的大盆。我也像旁人一样把碗放到桌沿,以表示要馒头。师傅给了一个馒头,我要把碗缩回,动作却迟了,又得一馒头。毫无经验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下咽。但我高估了自己的胃口,一来北方人的食量本来就比南方人大,二来舟车劳顿之后,食欲不振。当众人都碗底朝天了,我还在和饭食作艰苦斗争。想想吃不下就算了吧,却见一个行堂的师傅在嘱咐我旁边的女孩,请她把碗里剩余的饭粒吃尽,我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知道今天没那么容易过关了。
忽然有人起来诵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我鼓着嘴,尴尬不已。诵经毕,众人照样鱼贯而出,只有我对着吃不完的东西发愁,又不愿一溜了之。无奈之下,捧着碗去请求行堂师傅。师傅的眼神并不严厉,只说:这不是吃完吃不完的问题,而是因果,有饭吃是福报,要惜福。
小时候老师也常教导“要爱惜粮食”,但“惜福”一说是近来看弘一法师的讲演稿才领会的。他在《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中说:“我们即使有十分的福气,也只好享受二、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诸位或者能发大心,愿以我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那就更好了!”
有福气尚且应存布施之心,浪费就更不应该了。我明白这个道理,胃不明白。师傅见我为难,就宽和地建议我把饭菜带回去,慢慢吃完。
我捧了饭碗回寮房,真担心自己不行。回去把饭菜倒进杯子里,用开水泡了,坐下一口一口地吞咽。室友们大都是北方人,饭量并不让她们为难,而她们都很理解并且鼓励我。我终于把泡了水的饭菜都吃完了,虽然觉得饱胀,但当杯子里最后一滴汤水喝尽时,一种喜悦在心里油然而生。我清晰地感觉着这个喜悦的升起,虽然只是一件吃饭小事,却是收束自己放纵之心的开始,是完成本分之事的释然,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
这是我在柏林禅寺吃的第一顿饭,也是柏林禅寺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酣畅的午睡之后,傍晚时分,和室友媛媛去参加晚课。穿过重重的回廊,我们去万佛楼。这时我才细细地观察柏林寺的回廊,从你站立的这一个点,蔓延到四面八方,犹如一首长诗,一唱三叹,曲折回旋。而它的设计也蕴涵着细腻的慈悲,无论你从寺院的哪个地方,要去任何其他地方,都可以在廊下走,它的檐顶都可以荫蔽你,让阳光雨露在你视线之内,却在身体之外。
当万佛楼尽现眼前时,我们一时屏息。回廊之外,宽阔的平地之外,三座巍峨佛楼庄严坐落。中间最高一座正是万佛楼,三重广檐,比起明清建筑之颠的故宫城楼毫不逊色。两旁连接着文殊阁和普贤阁,让人想起佛陀身边的胁侍菩萨,相映成辉。第一眼看去,在惊讶赞叹的刹那,身口意都融合在那一刹那,没有了其他杂念思维,这一瞬间,或许就是当下的清净吧!
入内依次站立,钟磐响起,晚课便开始了。僧人们唱诵的声音宽广洪亮,穿云裂石,绕梁氤氲,似乎有渗透十方三界的力量。万佛楼的内部空间很大,容纳的佛像有万尊之众,正面五尊大佛,各结不同的手印,但那无所不包容的眼神却是一样的。无数小佛像分列两边,对称整齐,严丝合缝,汇成慈悲海。
殿堂中央,明海大和尚礼拜诸佛。早先就听说,明海在俗时是北大的高才生,很年轻就出家了,因而有些传奇色彩。他有一双细长的凤眼,时常低垂,谦和而自成高贵。只有眼角的细纹泄露了他也是身在人间,岁月也会在那淡静的面容上留下刻痕。当他躬身下拜时,他的身体竟像云门舞般轻盈柔软,当他敬立时,那内外通透的气度,却比群山更庄严静默。让人想起《世说新语》中对嵇康的形容:“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当他专注内省,身边的外物仿佛空幻,而周遭的灯火、经幡、钟鼓、群僧,却又似乎在他眉宇间被尽数包容。
这是我第一次仔细体味出家人的风范,以前一直很好奇,觉得僧人都过着高深莫测的生活,性情也必定独特。在我这个俗人看来,明海好像把一切都展现在你面前了,但你仍觉得他是个谜。他们都是谜。
但无论谜面如何扑朔,谜底却只有一个。
在《天下赵州生活禅》里,马明博先生记录了净慧老和尚在筹建万佛楼时所倾注的心血,有老和尚的诗为证:
经行不忍见高楼,每见高楼事事愁。
昨日买砖钱未付,今朝钢价又抬头。
……
万人同建万佛楼,赤手空拳费运筹。
铁架擎天赀费急,羞囊无机暗生愁。
一个自幼修行、德高望重的出家人,似乎是忘怀人境、不染纤尘的,却要“不忍见”、“事事愁”、“暗生愁”,为的并不是自己。也正是这位出家人,复兴柏林寺时为了钱奔波伤神,当柏林寺庄严崛起时,却免收寺院门票,广纳众生,还号召全国寺院免费对外开放。
谜底便是向佛的赤心。
雁鸟疾飞,季节变易
沿着河流我慢慢向南寻去
曾刻过木质观音浑圆的手
也曾细雕过 一座隋朝石佛微笑的唇
迸飞的碎粒之后 逐渐呈现
那心中最亲爱与最熟悉的轮廓
在巨大阴冷的石窟里
我是谦卑无怨的工匠
生生世世反复描摹
——席慕蓉《历史博物馆》 |